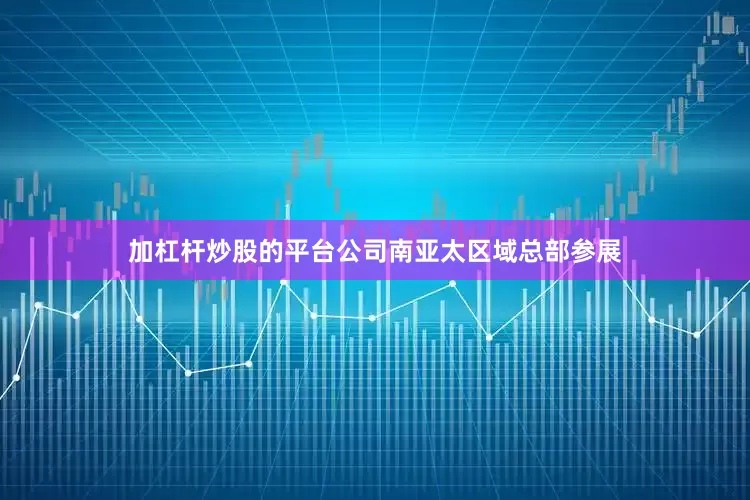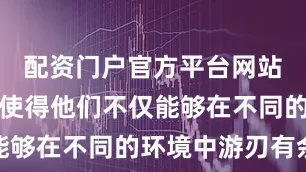本文为清代医家张璐的观点
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讲标本关系,可谓是中医辨证的精髓。要治得准,就得看得清到底是治“根”还是解“表”,是先治本、还是先处理急症。很多医家讲标本,但往往只说个顺序,仲景则讲得透彻,从一病、两病、传经,到一经、一身的标本关系,举例实用,讲法精准,今天整理下来,能帮临床厘清思路不少。
先说“一病”的标本。就拿太阳中风来说,最初怕冷是根,是“本”,后来的发热是“标”,所以治疗上要从“本”入手。再比如阳明热病的白虎汤证,病人嘴干、心烦是“本”,背部微恶寒是“标”,这时候也不能光顾着解表,要清内热才行。这就是典型的“治本不治标”的思路。病的关键在哪里,药就下在哪里,不能被表象迷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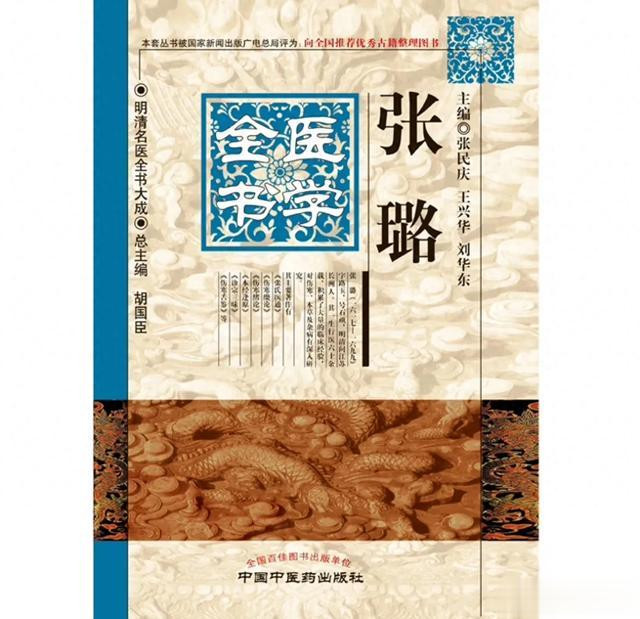
再看“两病”的标本。有的人体内藏着伏邪,突然又感了外邪,两种病一起出现。这种情况下,伏气是“本”,新感是“标”,治的时候要用凉膈散清里热,同时加点葱豉来散外邪,就是“治本兼治标”。或者病人本来脾胃虚,后来外感风邪,虚是根,风是表,要用补中益气汤来补虚,再加点羌活防风来解表,这样才能标本兼顾。只顾一个,另一个就会出乱子。
传经过程中的标本关系也不能忽视。比如太阳病初起时,发汗没发透,邪气没解净,转而传入阳明,这时太阳就是“本”,阳明是“标”。治疗时,仍要从太阳入手,用葛根汤加麻黄,才能既顾到传变后的新证,又不忘本经之邪。如果只顾阳明热,不管太阳未解,那就容易治标不治本,后患无穷。
还有“一经”里的标本问题。比如太阳病初起头痛发热自汗,这是桂枝证,是“本病”。但病了六七天还不好,出现烦渴、爱喝水,说明邪气已经入了膀胱变成了五苓散证,这就是“标病”。这种情况就不能只靠桂枝汤,而要加五苓散,两个一块用,才能本标兼治。这种情况临床很常见,病拖久了症状就复杂了,要根据新证灵活处理。

更复杂的是“一身”的标本问题。有的病人全身发热,结果反而喜欢穿厚衣服,这种不是热证,而是“寒在骨髓”,阳气虚,热浮于外,这是“标热本寒”;要用小建中汤加黄芪来扶正。反过来,有的人浑身发冷,但不愿穿衣服,这反而是“标寒本热”,寒在皮肤,热郁于内,要用桂枝汤加黄芩来调和。这种寒热错杂,必须从内到外分析,不能只看表象开药。
仲景还特别讲到一些“寒热错乱”的特殊证,比如夏天大热天,有人非但不怕热,反而想穿衣服,这不是中暑,而是阳气虚,阳虚则外寒,得用附子理中汤加黄连来调和寒热;冬天大冷,有人却爱脱衣服,这不是阳盛,而是阴虚内热,用竹叶石膏加附子才合适。这些都是看似不合常理,实则有内因的证,治法上不是简单地从寒热表里来区分,而是“从中治”,这是仲景独到之处。
最后再说说“先后顺序”的标本判断。有些人初起受寒,身痛是“本病”;医生误下后,出现下利清谷,这成了“标病”。这时候,虽然腹泻看起来严重,但根子在表,不能一味治泻。得先用四逆汤救里,再回过头用桂枝汤解表。先后顺序,决定了治疗次第。有些医书讲“先标后本”,仲景则根据证来,不拘一格,什么时候该解表就解表,什么时候该救里就救里,灵活变通,这才是真正的活法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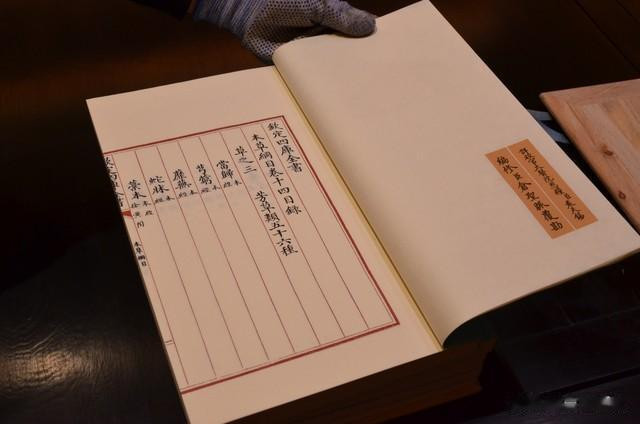
标本法绝不是机械的先后顺序,也不是表里冷热的对立,而是一种根据病情变化做出的权衡取舍。有的只治本,有的兼治标;有的从本治标,有的随证施治。这些思路若能吃透,临床上处理复杂病证时就不会慌乱,也不会一味追求“清热解表”“扶阳补阴”这些泛泛之谈,而是真正做到因病设法、因证用药,活用《伤寒论》,治病有章法。
传金所配资-安全股票配资公司-可靠股票配资网-配资网站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